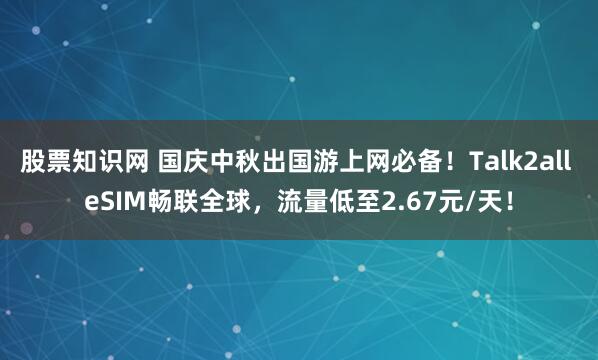“1953年6月17日上午十点股票知识网,车上那位同志是你们市里的人吗?”陈赓在市委大院门口把卫士叫住,声音不高,却透着火药味。
陈赓此行原本是到哈尔滨市政府商量哈军工配套工程用地。一路上他思绪纷乱:学院建设,工地物资,时间紧迫。谁知刚进市区,汽车就被一名交警拦下,对方不由分说钻进车厢,还嚷嚷着“去警察局”——那股子“官老爷”腔调,立刻惹恼了老将军。到了门口,陈赓一句“这是你的兵”便把火丢给了市长吕其恩。
吕其恩赶来时,鞋还没系好。他知道陈赓脾气耿直,先敬个礼,再把人带到会客室。陈赓把过程复述一遍,末了丢下一句:“军民一家,可不能有人端着架子。”话音落地,屋里顿时冷场。吕其恩点头、记下、送客,表面云淡风轻,心里却掀起浪。

这件小插曲之所以能激起陈赓怒火,并非偶然。哈军工是“一号工程”,中央要求军地协同。陈赓深知,若地方部门作风不好,再好的蓝图也会打折。而吕其恩同样明白:城市建设不是空中楼阁,先得有人干、肯干、会干。
追溯吕其恩的履历,他不是科班出身的官僚。1911年生在胶东渔村,少年爱下海摸鱼。九一八后,他扔掉渔网,跑到烟台、北平求学,接触马克思主义。1933年,筹办读书会,被宪兵查封;1935年,在北平地下党领到第一张入党介绍信。打那以后,他成了“交通员”“联络员”,白天学生、晚上专递密件。
七年抗战、四年内战,吕其恩踏遍胶东山海。为组织起义,他披蓑衣、划小船,敲渔号暗联队伍;为护送干部,他摆渡夜航,绕开日军封锁。1945年作为七大代表进延安,又被派回东北从事地下工作,练就一副“急事沉住气,难事豁得出”的性子。

朝鲜战争爆发后,他在志愿军后勤部忙到脱相。烈士陵园里埋着他几十个老战友,他没流泪,只写下一句话:“后勤若断,前线白打。”战后被调任哈尔滨市长,他把“后勤思维”带进市政:城市即战场,民生就是弹药,干部作风就是军纪。
也难怪陈赓一发火,他听得出吕其恩的念头——“抓风气”。第二天一早,市政府派出调查组,三天之内查出交警队互相揩油、拦车“搭顺风”已成惯例。吕其恩借题发挥,发动机关干部写自查报告,会上直言:“谁把自己当成老爷,就别在这儿领政府的饷。”不少人脸色煞白。
治理作风只是第一步。陈赓需要土地、电力、建筑劳力;市里则需要技术、资金、人才培训,一拍即合。为免文来文往耗时,两人干脆定了“红线电话”:军工院两圈、市府三圈,铃声不同,一接通就对事不对人。有人私下调侃,“这电话比内线还内线”。
有意思的是,吕其恩对苏联城市规划既学又挑。1950年赴苏半年,他看了莫斯科宽阔大道,也看了列宁格勒下水系统。回国后提出:哈尔滨纬度高,街道不宜过宽,要留出冬季堆雪槽;同时住宅楼底层加设锅炉房,供热管线不穿马路,以免冻裂。这些细节,大大节省了后续维护费用。

1954年春,哈军工一期交付。陈赓特意请吕其恩剪彩,两位老兵并肩站在大礼堂前,风把衣角吹得猎猎作响。陈赓低声说:“那天我冲你发火,不好意思。”吕其恩摆摆手:“动真格才像咱解放军。”一句玩笑,却把军地情谊拉得更近。
哈尔滨的变化肉眼可见:工厂烟囱日夜不歇,松花江铁桥车轮如织。市里还悄悄种下十万株西伯利亚榆树,据说是吕其恩拍板——“树长得慢,但遮阴最长”。几年后,人们终于在盛夏找到了纳凉的去处。
1957年冬,哈尔滨首届冰灯游园会试办。有人向上级打报告,“劳民伤财,不宜铺张”。问到市里,吕其恩只回了两行字:“冰雪是我们的资源。节日是人民的节日。”批示简短,态度却坚决。此后,“冰灯”逐渐升级为“冰雪节”,几十年后成了城市金字招牌。

吕其恩在哈尔滨一干二十七载,从重工业到轻纺,从自来水扩容到污水处理,样样过问。“开会不长过一支烟”“批示不一句空话”,这是老同事们的印象。1979年7月18日,吕其恩因病离世。那天江畔凉风乍起,市民自发停步致哀。有人回忆:“他把苏联的图纸改成了哈尔滨的样子,也把官气改成了干劲。”
再看1953年的那场小风波,一位交警的横行,让陈赓炸了雷,也促成市府一次痛快的自我刮骨。或许历史总是如此:几个看似不起眼的瞬间,折射出新政权如何塑形、如何校纪、如何把“为人民服务”落在地面。风雪城市里,那句“这是你的兵,该管管了”,至今听来仍掷地作响。
光瑞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